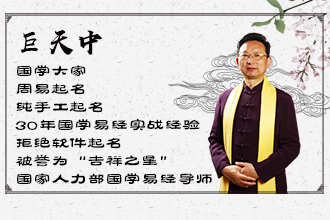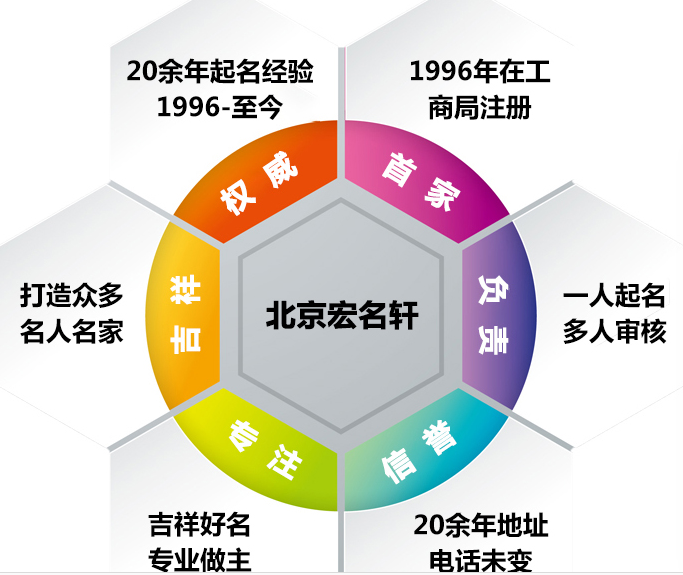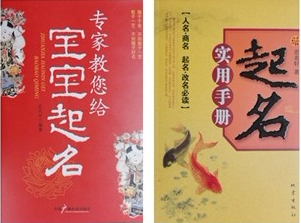在一些书面和口头语言中,人们习惯上称“风水术”为“封建迷信”。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风水现象就已产生,其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人类聚落的发生早期。
风水是古代先民为选择理想的生活环境而形成的一门学问。早在原始社会,风水现象就已产生,其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人类取落的发生早期。
中国风水文化,实质是中国人在居住部题上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死总是以及人的生死与建筑环境的关系问题。人类一旦诞生,就自然地产生了人类的生存活动及其死亡与自然环境和随后发生的人类与其居住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天人关系、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风水观念及其在建筑艺术中的运用,体现出中国人所一向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居住环境以及由活人所联想的死人与自然环境、墓葬形式之间的和谐境界。
风水强调“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观念并行不悖的文化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民居、村落、城市及葬地环境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风水”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最早见于《葬书》。《葬书》是一部专论如何选择葬地环境的着作,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又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首次提出了明确的以“藏风”、“得水”为条件的“风水”概念,为后世的“风水”概念所传承。
远古朴素风水观源于古代先民居住实践
从考古发掘来看,仰韶文化时期聚落位置的选择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倾向。具体表现是:
①选择在河流附近,不仅便于取水,而且便于农业生产的开展;
②处于河流交汇处,交通往来便宜;
③处于河流阶地上,既有肥沃的耕作土壤,又能避免洪水的侵害;
④坐北朝南,便于自然采光。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这些远古村落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叠压,如河南淇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长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这说明多数古聚落基址的选择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同时表明在六七千年前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认识已有了较高的水平。
距今约一万八千余年的中国北京“山顶洞人”,住在自然的“山顶洞”里,该洞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从对该洞内部空间功能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见出,当时的北京猿人似乎已有朦胧的“风水”意识,洞内可分为“上室”、“下室”与“下窨”三部分。上室位于洞穴东半部分,面积约为110平方米,比较宽敞,地势较高,是生人居住的地方,这从地面上至今残存的一堆用火灰烬可以见出。下室位于洞穴西半部,地势稍低,这里有人的完整残骸留存,且在人体残骸周围散布象征生命、鲜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痕迹。下窨地势比下室更低,南北长3米,东西宽1米,是一条南北向的自然形成的裂沟,这里丢弃着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从这三个功能性分区来看,“山顶洞人”在居住问题上对生人与死人的“居住”方式处理是有区别的。生人在上而死人在下,生人居东而死人居西,但对死者残骸也并非随意处置,残骸周围象征生命与鲜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在处理人的葬所问题上,已经不自觉地遵循了后世中国陵墓风水文化的一条原则,即“事死如事生”。对于“山顶洞人”来说,死是不吉利的,但那时已经萌生了“死乃生之始”的原始文化观念。这里,上室与下室的划分,实际是后世风水术中阳宅与阴宅的文化雏型。而动物残骸埋于地位更低的下窨之处,已经体现出入比动物的高贵。
仰韶建筑遗址中的原始风水术的初朦
从考古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营造活动已注意到如下几点:
①环境:地质条件好,近水。“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新中国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第54页)如西安半坡遗址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沪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即使铲河水位暴涨也不致危及聚落。
②方位:朝阳。房屋基址大体朝南或向东,如半坡中间的大房子朝东,围绕大房子的氏族成员住的房子多朝南,这可能是上述中国古代“喜东南厌西北”的自然观的体现。
③分区:遗址四周有防御性壕沟。沟北或南有公共墓地,居住与墓地分开。
这些聚落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建立在对地理环境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此外还具备了方位的概念,懂得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这种聚落布局模式实可归纳为四个宇——“近水向阳”,这也正是后世风水孜孜以求的基本模式早期先民的“卜宅”与“相宅”
新石器时代对原始取落位置的选择,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体现了先民们在观察周围环境的同时,开始有了能动选择和适应的能力。
在考古资料之外,大量的甲骨卜矢,也记录着早期先民的“卜宅”实践。殷代卜筮活动盛行,事无巨细,皆要卜定,因此留下大量关于建房、造宅的“卜宅”龟辞,如:
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已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
上辞表明殷王要修城邑,卜问建在何处为当。验辞认为应建在唐(地名),于是有“我从,之(兹)唐”,即我原听从上天的旨意,将城邑建在唐。
又如,殷王想在鹿(地名)之东北修城邑,反复多次卜问是否可行,卜辞是:
已亥卜,丙贞:王屮(有)石才(在)鹿北东,乍(作)邑于之(兹)?
王屮(有)[石]才(在)鹿北东,乍(作)邑之(兹)?乍(作)邑于鹿?(《乙》三二一二)
这类“卜宅”之辞难以枚举,从卜辞内容可知,当时“卜宅”的格式是:“卜日—卜—贞人—贞事—兆—在某月—卜地—中左右之屯聚也。”卜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点:何时为吉,何地为吉。“卜宅”是一种消极的“环境选择”方式,人听信于卜问的结果,带有较大的或然性。
这种用占卜方法以决定建筑营造的风水之术,在周代也很盛行。留存至今的详细记录占筮的《周易》,关于居处及家庭生活的占筮达二十余例。风水之术被称为相宅,相是观看,是对象与主休相互“相中的意思。
在《诗经》中,“相宅”不叫“相宅”,而叫“胥宇”。如《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这里,“胥”的意思即为审视、相看。
在有关“胥宇”即相宅的早期文献中,最为后世堪舆家所推崇的是《诗经大雅·公刘》: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陟则在献,复降在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浦原,乃陟南冈,乃观于京。京师之里,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既浦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从这儿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见,为人笃厚、德高望重的氏族首领兼术士——公刘,为“胥宇”,时而“陟冈”,时面“降原”,时面“逝水”,时面“观京”其过程与后世堪舆家们的相地四部曲——觅龙、察砂、观水、点穴——颇有相通之处。
还有,《诗经·大雅·绵》写道:“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周原是周族的发祥之地。这也说明,周族祖先在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时,是看过风水的。
《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淮南子·本经》说:积壤而丘处。“《孟子·尽心》说:“得乎丘民为天子。”《庄子·则阳》说:“何谓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凡此所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所谓丘处,所谓丘民与丘里者,都说得是古人有居丘之俗。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vski)在《巫术科学宗都与神话》一书里强调:原始人的生活中既有神秘的痴狂亦有理智的科学。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古代中国人已发明出“土圭法”、“土宜法”、“土会法”等一系列上究天文下察地理的方法,从而使卜宅这一活动上升为一种辨方相土观水的相宅实践:“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周礼·夏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土方氏掌理土圭的官法,以测日影,量度土地,测定方位,选择可以居住的地方,建立邦国都鄙,明了土质所适宜种植和变化土质的官法。授给任土力制贡赋的载师们,王者巡守,在止缩的行宫周围树立木材作为藩篱。“土圭法”、“土会法”、“土宜法”是生活、农牧业生产经验的结晶,已闪现出某些科学智慧的曙光,从而赋予相宅活动以前科学的含意。
从《诗经》的某些“相宅”记载可以见出,周人已在对自然地形、地理地貌,环境进行初步的具有朴素理性的审视与相度,这时相宅已逐渐摆脱初期巫术的虚幻,增添了实际内容,道德是根据自然条件选择合宜的地基,然后根据土圭法确定建筑的朝向。这种择基与立向正是后代风水中“形法”与“理法”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