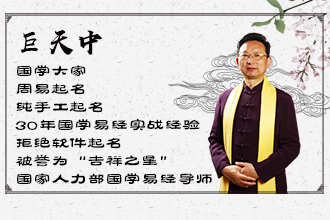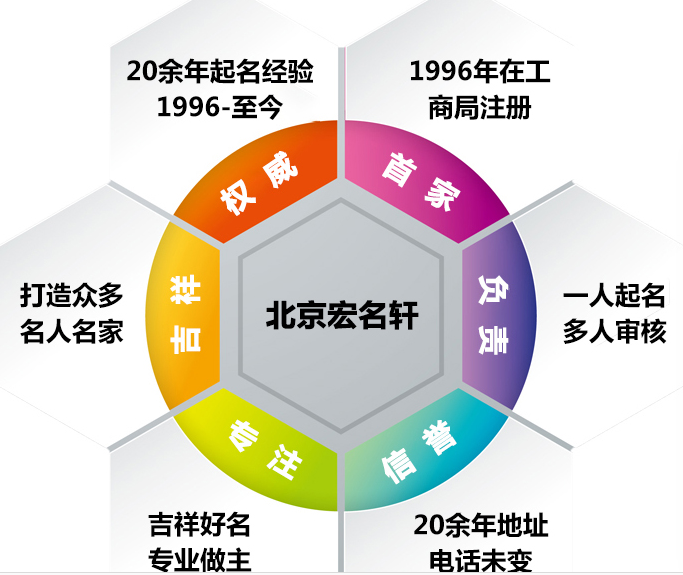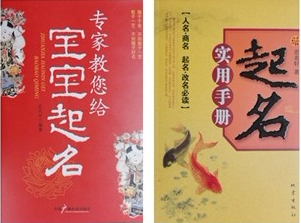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他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他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霞客与风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明末清初的考古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做了有益的探讨。
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此书在清代268年里默默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饰四篇;卷二讲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问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计成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璋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控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因为战事还没有结束,只好作罢。
后来,明成祖把都城迁到北京。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如天坛圜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其朝向很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大殿、华盖殿、谨身殿三殿的基座呈“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
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时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殓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亘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如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桢,他被封为楚昭王,就藩武昌达54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术士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哙“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妃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上。
明代,一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晁氏九经堂遗址,临终前令子买下,把自己葬在旁边,据说,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
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佑,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人匾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依山傍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